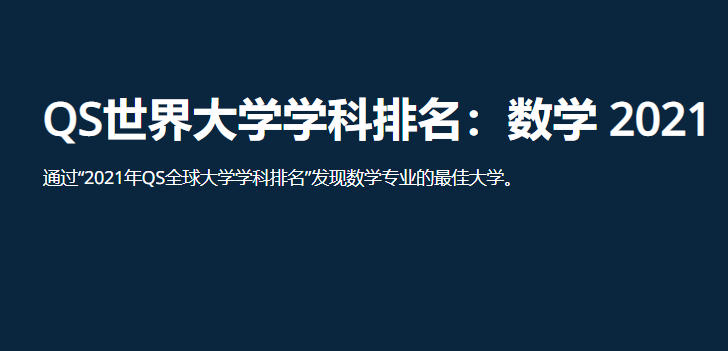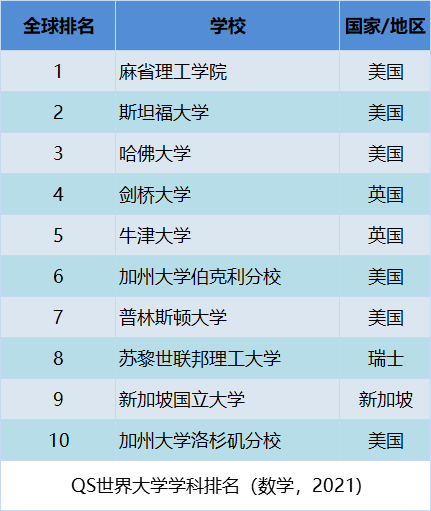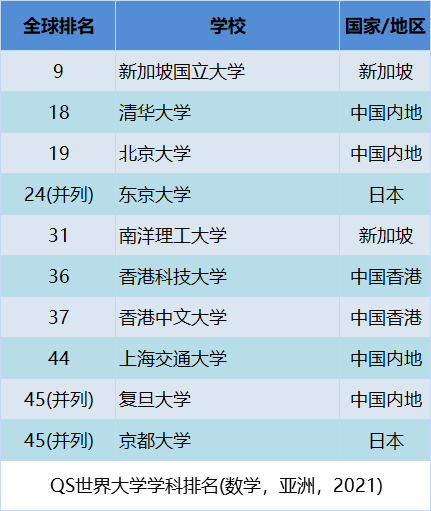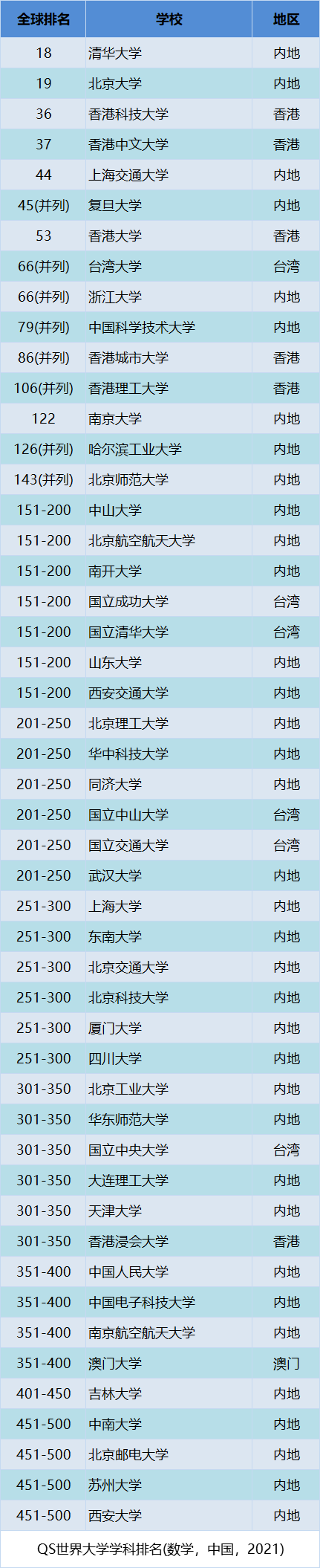智慧与美貌并存:三八节给你推荐一位美女数学家吧
关注 哆嗒数学网 每天获得更多数学趣文
米歇尔·奥丁说出了我的心声:“尽管数学家几乎不知道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卡娅的作品,但他们都看过她的肖像。”我曾经在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卡娅的纪念活动中,去帮助女孩子们,让她们对学数学产生兴趣。我知道科瓦列夫斯卡娅是一位开创性的女数学家,但是我对她的生活和工作的细节却是一无所知。
当我偶然发现奥丁的《纪念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卡娅》(Remembering Sofya Kovalevskaya)一书时(2008年以法语出版,2011年以英语出版),我决定是时候纠正这种状况了。这本书不是一本普通的数学家传记。正如奥丁在引言中所写,这本书不是一本历史书,它也不是一本数学书或者一本小说。这是一个不拘一格的、独特的作品,它不屑于一个简单的标签。当你读的时候把你的期望放在一边。用《Marcel the Shell》里一句智慧的话来说,“真的,你只要搭个便车就行了。”

1850年,科瓦列夫斯卡娅在莫斯科出生。1868年,她步入了一场交易性的婚姻,因此她离开了俄罗斯,最终跟随柏林大学著名的数学家卡尔·魏尔斯特拉斯学习数学。因为柏林大学不招收女学生,所以卡尔·魏尔斯特拉斯私下里教她。1874年,她在缺席的情况下获得了哥廷根大学的博士学位。拿到学位后,几年内她没有找到工作,并且生下了女儿。最后,在米塔-列夫勒的努力帮助下,科瓦列夫斯卡娅在斯德哥尔摩找到了一份私人教师的工作(一个学术级别低于教授的职位)。1888年,她获得了一项殊荣,这使她有可能在斯德哥尔摩获得教授的永久职位。不幸的是,在那不久之后她就死了。她精通多种语言,无论是俄语、波兰语、法语、德语、英语还是瑞典语。除了数学事业外,她还会写小说和戏剧。
就算现在看来,她的职业生涯也很现代化,我被震撼了。奥丁写道:“毫无疑问,她是第一个以我们今天所理解方式从事大学学术职位的女性:她通过定理证明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她教授课程,关注政治,她深信着科学家应该肩负的责任,她到处旅行,她证明了更多的定理,她参加委员会会议(但没有太大的热情),她有一个女儿,她是国际期刊(Acta Mathematica)的编辑,她为妇女的权利而战,她参加并为科学会议做出贡献,她准备升职,她写了很多报告和推荐信,她远道而来与其他大学的同事见面”她非但没有因为是个女人而成为贱民,相反,她成为了数学界受人尊敬的一员。
科瓦列夫斯卡娅在广泛的分析领域研究了几个问题。她的博士论文包括三篇关于三个不同主题的论文,任何一篇都足以独立获得学位。它们涵盖了偏微分方程、阿贝尔函数和土星环的形状。她晚年最重要的工作是研究像陀螺一样的旋转(也就是说,在一个点保持固定的情况下的转动)。欧拉和拉格朗日解出了两种最简单的“陀螺”,科瓦列夫斯卡娅发现了另一种可以被分析的“陀螺”。正是这部作品为她赢得了1888年的勃丁奖。奥丁通过科瓦列夫斯卡娅的“陀螺”与科瓦列夫斯卡娅邂逅,并在涉及科瓦列夫斯卡娅关于这个问题的工作的章节中深入到了数学的核心细节。
尽管科瓦列夫斯卡娅取得了成功,但她确实遇到了困难,她的声誉也因此经历了起起伏伏。其中造成声誉受损的原因,有一些是因为在她死后,她的一篇论文被发现有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是一个不幸的情况,即使是有成就的,细心的研究人员偶尔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有一些是由于人们对妇女的角色和行为的偏见。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碰巧重读了弗朗西斯·苏的《人类繁荣的数学》,这是他在一月份作为即将退休的美国数学协会主席发表的演讲。在演讲稿中,他引用哲学家西蒙娜·韦伊(数学家安德烈·韦伊的妹妹)的话“每一个人都在为了被不同地解读而发出无声的呼喊”并对此进行了反思。
奥丁的书不仅讲述了科瓦列夫斯卡娅与数学家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也用同样的篇幅讲述了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奥丁列举了她所面临的一些侮辱,以及她的名誉仍然面临的问题—她为了能够学习数学、能有离开俄罗斯的自由而进入的“白人”婚姻,她的薪水问题,关于她是否真的能够独立于她的顾问卡尔·魏尔斯特拉斯的陆续而来的问题,关于她的外表的没完没了的评论—我无声地呼喊着希望科瓦列夫斯卡娅能够以不同的角度被解读。她不应该成为其他人对女性和数学家应该是什么的预测的画布。在第11章“我记得索菲娅,乔治、约斯塔、茱莉亚和所有其他人写的”中,这种感觉最为辛酸。在其中,奥丁收集了一些生前认识科瓦列夫斯卡娅的人和她死后通过名誉和谣言认识她的人所写的有关科瓦列夫斯卡娅的信件或其他文字。
例如,奥丁的书中包括了摘录自卡尔·魏尔斯特拉斯的另一位学生卡尔·龙格的一封信:
星期六我们在她的公寓举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聚会。聚会由科瓦列夫斯卡娅太太和四位年轻的数学家组成,我们像往常一样交谈。她大约30岁,面容娇嫩,她很体贴,还有点悲伤(距离弗拉基米尔(科瓦列夫斯卡娅的丈夫)自杀已经有两个月了),她微笑时相当迷人。对我来说,和一位女士谈论数学并能完全自由地畅谈是很奇怪的。她对这方面的问题很了解。我知道这一点,尤其是当她就着我的工作,提出了很有价值的问题的时候。在这之前,我曾想象过她可能是个鼻子尖锐,长相古板,戴着眼镜的人,但我惊奇地发现,科学教育竟能与如此完美的女性气质相提并论[原文如此]
正如奥丁费尽心力所观察到的,龙格对科瓦列夫斯卡娅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和一位有魅力的女性的惊讶表明,“这种刻板印象可以存在于物种之前。”一次又一次地阅读回忆,我觉得科瓦列夫斯卡娅正被其他人的观念和信念所掩埋。
科瓦列夫斯卡娅和两位数学界的早期女性苏菲·姬曼、艾米·诺特一样,都是英年早逝。当她在热那亚和斯德哥尔摩之间旅行时感染肺炎时,年仅41岁。关于那个故事,奥丁写道:
在丹麦,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天空飘着雨雪。火车站台上有风,渡轮上也有风,风从一个地方呼呼地一路吹到另一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当索菲娅到达斯德哥尔摩时,她病了。一开始病情并不明显,因为她在2月6日(星期五)教这学期的第一节课,然后她去参加了天文台的一个聚会,因为发烧,她提前离开了,之后,她还乘错了公共汽车,那时候的天气非常寒冷……之后,她变得更糟了,就上床睡觉了。周一,她看起来似乎好多了,她和米塔格·莱夫勒谈论了她对欧拉方程的看法……但是她的病已经转变成了肺炎,那时是在19世纪,比发现青霉素的时候早了40年……即使你是41岁的杰出科学家,即使你有很多科学、个人和文学方面的计划,你还是死在了肺炎的手上。正如索菲娅所说,正如她生病前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即使你很快乐,你也会死,就像那时的索菲娅一样,然后,就是索菲娅所做的那样,她最终死于肺炎。
奥丁独特的表达使《怀念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卡娅》成为一本引人入胜的、感人的书。它不是传统传记的替代品,但对于任何有兴趣从另一个角度看待科瓦列夫斯卡娅的人来说,它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读物。
正如奥丁在书中指出,存在着许多不同版本的音译的科瓦列夫斯卡娃的名字,但他更喜欢拼写成“Sofya Kovalevskaya”。在这篇评论中,我大部分都是跟随奥丁的脚步,使用了“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卡娅”
关注 哆嗒数学网 每天获得更多数学趣文